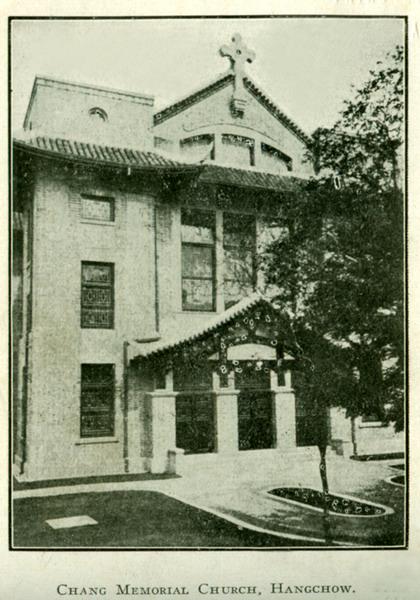
2013年之后的十年,是中国教会建制比较关键的十年,说这段时间比较关键,是因为在经济层面的转型后,政治治理秩序也日趋现代化。而传统教会的简直模式大都部那么“现代化”,急需在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做出调整。本文分析的教会不包括天主教,而只是定位在基督新教领域内。在过去的60年,新教在中国分为了两类,一类是三自教会,一类是家庭教会,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在政府登记。
“教会之外别无拯救”,从三世纪的居普良到16世纪的加尔文,对此都十分赞同,但是,他们所指的教会是使徒信经里的“圣而公之教会”,即在早期教会所在的1-6世纪,与灵智人教会相对立的大公教会,换句话说就是普世教会。于是,在中国,这个“大公教会”是缺席了,更于是,我们都在教会的救恩之外了。所以,建立与普世教会对接的总会,是当前当务之急。在过去,无论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都没有把建立总会考虑到自己的酵牧事工里。所以,三自教会并不垂直管辖,家庭教会的大团队,也只是简单的家长制抱团取暖,没有在加尔文和居普良的教会意义上适应教会一词。
那么,教会建制的思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北美教牧神学“plant a church”,即“植堂”才开始。而汉语教会是继承所谓“植堂”理念的。那么,认信大公教会的“使徒信经”的中国汉语教会,该如何同时体认居普良和加尔文的教会观呢。是建立总会,一种denomination性质的总会,denomination是1648年开始,在此之前,植堂根本无从说起。说到底,是第二代经院改教家背叛了路德和加尔文,极端分离的福克斯和再浸信派打败了长老制,所以,所以,深谙现代性反叛之道的大众信徒,自下而上的造了普世教会的反。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一个缺失了总会输出价值的普世教会中,怎么重建这种上帝认可的大一统呢。简单说,就是再建立总会。不过,2014年的中国,分众趋向已经很明显,任何一种理念或者价值都无法赢得大众了。所以,总会的建立,必须基于对小众化的分众趋势的理解之上。
在此之前的中国大团队,大部分是,一种是家长制,即总会掌握所有的财权和事权,各地方堂会处于弱势,第二种是民主和科学精神影响之下的城市教会团队,由各个地方堂会派出代表,代表总成总会,总会选举常务委员。这种比之于家长制更为落后,因为,这类总会没有自己专属的行政阶层,地方教会的离心倾向极浓烈。所以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在此后的十年内,“多中心治理总会”的模式,将成为最为合理的总会组成。这种“多中心治理总会”的模式,如下所述。
1、总会和地方堂会的关系
体现这种关系的是财权和事权,建立总会使得地方教会一部分的权利让渡给总会,但是两者权利分配的比例是如何呢。在现代化的教会建制模式里面,总会的财权和事权的比例大概为7:3。在依靠海外援助为主的过去的所谓“团队”中,一般不存在堂会向总会上交“会费”。但是在堂会日趋独立的未来中国,这种体现总会和地方堂会治理关系的财权和事权的划分,开始提上日程。一般而言,各个堂会的总收入保留三成比例用于日常运营,剩余部分上交。但是,这种财务管理制度,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有的是每月日常运营的后的结余款项上交,有的是按照教会收入“事项”,比如十分之一上交,但是地方教会的专项奉献自己留出来,用于“教会发展”。
总会既然拥有7成的事权,那么,事权在总会该怎么分配呢。按照以往中国教会的经验,有“约定俗成”的家长制“核心同工”用于管理和分配总会事权。但是,这种模式在小团队内部可以,随之中国国家层面治理秩序的完善,教会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必将出现庞大的地方堂会,这时候,单一中心的总会治理模式就不行了。而多中心治理总会,会成立事工部来形成总会之下的多种中心,这些事工部门用来治理庞大的地方堂会,而各个事工部对总会负责,总会会出席各个事工部的决策过程。
现在,几乎所有的地方堂会都已经自发形成某种松散的“联系”,在建立总会的时候,是一个地方堂会和总会利益进行博弈的过程。鉴于目前几乎都是家长制教会,教会都是在牧师的一人影响之下,所以,近似于削权的总会集成过程,变得极为困难。但是,作为转圆方式,可以采取过度,比如,事权和财权划分比例逐年调整,最开始,地方堂会只上交一年中一个月的收入,以后逐年提高。或者,总会参与教会分为两类,一类是总会“植堂”建立,这类教会总会直属直辖,而第二类教会是观察员教会,这类教会作为待加入成员出席总会各项事工。
作为多中心的各个事工部门,一般至少分为教牧基金会,负责牧师和总会办公室专职同工的工资和退休以及医疗保险等各项待遇,在目前汉语教会费用暂时短缺的情况下,可以按照比例和事项来逐步推进。二是神学教育事工,负责对总会所属牧师进行培训,目前在设立神学院困难的情况下,可以神学研讨会或者研究中心取代,三是,宣教事工部,负责植堂外宣,四是教务事工,负责监管牧师教义正确与否与按立新牧师。在刚开始,按立牧师的权利是属于总会,总会也在教义法理上拥有这种权利和义务,但是,在包括北美在内的各个国家,都出现了按牧事权的下调。这种原因是这样的,比如在最初的北美13块殖民地,各个堂会之间距离很近,各个堂会能轻松和方便的去总会开会,但是随之西进运动的教会的大觉醒,堂会越来越多,两级的总会建制不能满足堂会代表前来开会的便利。所以,就设置了四级分别为堂会、区会、大区会和总会。而按立牧师就授权给了区会,这种区会在韩国被称为老会。区会是由2个成熟堂会组成的。
2、韦伯总结现代政治的最大特点是出现了以政治为志业者,即科层官僚阶层,也就是专职行政人员。韦伯所说的这种古今之别是科层官僚阶层,这个阶层拿工资不世袭。而在此之前,欧洲的社会治理牧师是世袭的贵族来作为权利主角的,但是,在一个现代国家,科层制度出现了。这也是一个分众社会,如基督教的社团组织所必须的,所以,在多中心治理式总会中,必须有总会专职行政人员,那么,专职人员是才哪里来呢。是从各个事工部的议事委员会中产生,通过议事会议,锻炼了该人员的治理能力,为着总会的整体协调和召集做了预备。不过,所有这种议事规则和总会建制,都不保证民主和公义,但是无论总会建制的好坏和轻慢缓急,都有待上帝之手的悉心拨弄。
以上是简单的介绍了总会的建制结构,很肯定的是,对基督教这种NGO社团的越来越熟悉,使我们发现,只有这种教会建制,才能跟主流中的主流教会接轨,才能称为加尔文笔下有着救恩功能的大公教会。汉语教会在接下来,唯有进行此类的尝试,特别是现代行政学里面的多中心治理的尝试,才能成功,而这些国外同类教会的组织建构,是国内教会所缺乏的。尽管有人不敢承认,这类的总会,就是宗派意义上的教会联合体。假若有了这类总会,中国教会就能有自信跟世界主流教会进行交往和联系了,比如融入世界改革宗联盟的资格,就是成为一个认同新教传统下的加尔文理念一脉,而此一脉,就是宗派。开宗立派在汉语教会里是被神圣化的,但是,在实际的作用上,任何一个教会的联合体,任何一个总会,都有着宗派的意涵。如若真的能了解到这些,一个宗派井喷的汉语教会,未尝不好。
作者:张文龙,现居北京
(首发《古道》杂志)
感谢您的阅读!我们非常重视每一位读者的声音。若您在阅读过程中有任何想法、疑问、建议或其他想与作者交流的内容,或愿意帮助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处、提出改进建议,欢迎通过邮件(jidushibao@gmail.com)与我们分享。您的反馈不仅能帮助我们不断优化内容质量,也能让更多读者受益。我们会定期整理与回复大家的意见,优秀的建议还可能在后续更新中得到采纳。
反馈时,也请您具体指出是针对哪篇文章提出的意见与反馈。
期待与您保持互动,让内容在交流中不断完善。
立场声明
基督时报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基督时报保持中立。欢迎个人浏览转载,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版权声明
凡本网来源标注是“基督时报”的文章权归基督时报所有。未经基督时报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公共网站、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或引用本网图文。欢迎个体读者转载或分享于您个人的博客、微博、微信及其他社交媒体,但请务必清楚标明出处、作者与链接地址(URL)。其他公共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公共平台如需转载引用,请通过电子邮件(jidushibao@gmail.com)、电话 (021-6224 3972) 或微博(http://weibo.com/cnchristiantimes),微信(ChTimes)联络我们,得到授权方可转载或做其他使用。



